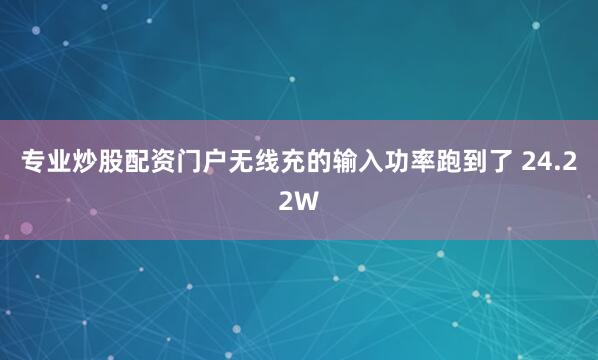张学良瞪着监视他的刘乙光,只顾看他身上的新军衔,却一句话都没吐。
过了几秒,他闷声说道:我估计这辈子都申请不到自由通行证了。

在1936年12月25日那天,张学良把蒋介石从西安弄回南京,到了晚上,他换上了普通人的衣服,然后就在蒋家门口被人给拐走了。
没有法庭,也没通知,老师一喊,“别动,锁喽!”
前两个月,张学良是被王方南看着的,这位哥们儿背景可不一般,军统出身,做事干脆利落,话也不多。
1937年3月,王老弟被搬走了,新来的负责人名儿叫刘乙光。
刘乙光,老家在湖南永兴,1899年出生,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的毕业生,跟黄克诚同班上课,这俩湖南佬经常一起抢盘子里的菜!
黄克诚后来走了条新路,刘乙光早年也试过这条路,先是加入了党,后来自己选择脱离,跑去跟军统混,越走越远。

接管张学良后,刘乙光当了个“张学良大人的办公室主任”,听着挺好听,其实干的活儿就是盯紧张学良,让他别想着溜达。
一开始是在浙江的溪口搞事情,特务负责里边儿的勾当,宪兵则在外围把守,张学良只能在一个小山庄活动,直径也就两百米不到。
出门得报备,吃饭要搭档,睡觉有伴房,看信得批准,写信得过审!
这套管理规矩可不是随便想出来的,都是按“重要的政治犯”标准来定的!
张学良虽然没被铁窗关,心里却像被铐住了一样,也没享受到一丝轻松。

刘乙真是个呆子,一天到晚就盯着那玩意儿,不嫌累啊!
吃饭的时候他在,张学良读书的时候他也在,连张学良洗脸刷牙,他都站那儿瞅着!
最开始,张学良还试着搭个话呢。
我想换身衣服,找老朋友聊聊,看看新书,听听东北那边的八卦,结果全都被拒绝了!
他恍若顿悟,这可不是临时工,是个长期的牢笼!
那天西安一大早,他骑上马儿进城,手里掂着把枪,耳边呼啦啦作响,这一下子搞得全国都在议论纷纷!
他连张信纸都得先请示上面,想见老妈一回还得写个报告求批准。
他脑袋上插了根杆子,硬是不认输!
他想溜走,结果每次都是头撞墙!
他发现旁边的刘乙光,简直就是个死板的老实人,干起事情来硬邦邦,一点情面都不留。

刘乙光每天都在写小本本,记录张学良的闲话、吃的是什么、心情咋样、身体棒不棒,然后每周把总结交给军统局。
张学良称他为“冷冰冰的人”,直言这家伙简直是一根疙瘩,连点温度都没有!
从西安的风头劲到浙江的山里福地,没过几个月,张学良一转身就从将军变成了铁窗里的小囚。

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,从1937到1946年,张学良像个踢足球的,总是东奔西跑换地方,刘乙光就像个贴身小跟班,哪儿都不离人。
山路坑坑洼洼他照样走,雪窦山冷得像冰箱他也不抱怨,搬家前一天就像打仗一样开始收拾,搬进去后亲自把每个门锁和窗户都摸一遍。
黄山、梅岭、萍乡、苏仙岭、凤凰山、修文、桐梓……这一串名字听着就像是开了个旅行大会,都是想让你在大自然里嗨翻天的地方!
张学良的走过的路就成了囚车的导航图,而刘乙光的工作一点儿没动摇。
日子就像一场无休止的斗殴,张学良家里的人寄来的衣服、零食和信件,有时候根本没见到影子,有时候一打开就发现全成霉菌乐园了!

他去找刘乙光,结果人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,说:“这儿被封了,不能乱走!”
再问一句,直接回你:”请您体谅规矩啊!“
张学良这脑袋瓜子真是转来!
有一次他给张治中写了封信,抱怨保安太严厉,求着换个看门的。
信刚写好,刘乙光一把抢过来,直言“这东西一发出去,大家就得开始瞎猜了,别发了!”
张学良气得脸都绿了,骂道:“你把我当成抢银行的家伙啊!”
有次连张学良也收到了老妈亲手写的信,结果信封看起来被人撕扯过,还重新黏上去了!
他拿着信件站了老半天,没动手撕开,不是怕让别人知道里面的秘密,而是被监视那股无力感压得连气都喘不上来。

1947年,台湾发生了“二二八”事件,弄得岛上乌烟瘴气,人人自危。
张学良突然被派去新竹的井上温泉,住进了一栋别墅,身边只带着一位保镖和刘乙光。
他心里想着:这儿咋回事啊,电话没听到、没人来看我,外面都是树,才意识到自己就像个“神秘失踪”一样!
后来才发现,有人提过一个“干掉张学良”的计划,可是谁把它搁下的就不清楚了。
张学良心里有点小疑惑,觉得刘乙光不太靠谱。
后来好多年后,他回忆起那时候,只是咕哝了句:“我每天晚上都紧张兮兮的,生怕有人推门进来,把我牵走,再也不让我回家。”

这心情,这么磨磨蹭蹭整整快十年了,刘乙光就是个沉默的石头。
他那本日记呀,几个月就写了那么几句话:“天冷得像个冰箱,将军的心情还不错”“外面没啥事,内部也挺稳”
他把张学良当成办事的小机器人,完全没把人当回事。
张学良从一开始想着能有啥好事,结果彻底醒悟自己早就被人抛到脑后了。
他曾经说过:“刘乙光盯着我,就像防守一支军队似的严密。”
后来说:“他就跟块大石头似的,把我和外面世界隔得严严实实!”

这俩人的关系僵到能拿冰箱里的冷空气来取暖,见面的时候连空气都开始掉温度。
张学良再怎么温和,也会怒掀饭桌,刘乙光默默无闻,第二天照样上班检查,按时陪着吃饭。
这嘎达僵了整整二十年,嫌麻烦!?
学良尝试过拼命,也试过妥协,可这个守卫,始终没给过一丝机会。
过了一段时间,张学良意识到,这家伙铁定留这儿,也没打算改变啥。

在1937年,刘乙光刚刚接管“张学良将军管理处”那会儿,他的军衔可是中校哦!
官儿不大,活儿可不少!
每份简报都得送到军统局,偶尔还得当面去跟戴笠唠唠。
三年都没到,他就像吃了长生不老药,飞升当上了上校。
在那个时候的军统里,这种升官的速度简直比火箭还快!

1940年,戴笠一拍脑袋,刘乙光被调到军统局总部当上了少将专员,依旧忙着张学良的那些事儿。
命令下来了,张学良瞅了眼他的军装,眉毛一挑,没吭声。
等几年过去,抗日战争一结束,张学良就被送到台湾去了。
护送的人里,刘乙光还在场呢!
这时候,他已经扛上了少将的肩章,身份从“处长”摇身一变成了“局里的大爷”。
张学良突然觉得这事儿不简单!
他不是被捉住关了一小会儿,而是被整得够呛,他心里明白,刘乙光一路飞升,说明自己再也别想混成大爷了。
军衔就像是信任的印章,越捯饬得漂漂亮亮,意味着上头的人越欢喜。
刘乙光这小子飞得飞快,说明他干得不错!
张学良曾跟蒋介石说:“我想去美国混日子,不想掺和那些政治的事,求个安静自在。”

他没想到的是,军统连个出口都不给他留!
某次内部会议上说:“张某虽然与外界断了联,但毒瘤还在,得继续盯着!”
刘乙光一年要跑台北三趟,递交的“安检报告”里全是琐碎的东西,比如咋避免联系、咋封锁信息、咋稳住情绪。
刘乙光对工作简直是个细致狂,字里行间都像是在做考卷,绝不放过一个标点!
张学良虽然啥都看不见,但军衔在他眼里亮堂堂的。
军衔就像是个招牌,甭管你说啥,先看看头上那玩意儿!
1946年,送到台湾的那晚,张学良站在基隆码头,一旁全是拿着枪的宪兵,感觉自己就像在拍电影。
他一转头,发现就刘乙光跟在后面,站得笔直,声音还是那么淡定。
上船之前,张学良扭过头,看了看刘乙光肩膀上的少将标志,心里瞬间清楚了:这次是跳不出这个圈儿了!

他一声不吭,晚上躺在船舱的床上,冷风刮得跟刀子一样,只喃喃道:“这次估计是要长待了!”
这话虽然没对任何人说,但周围的亲戚都凑耳朵听见了。
刘乙光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嘟囔:“将军心不慌,情绪像门口的石头一样稳!”
没怎么着急嘛。
其实没必要搞得那么欢脱,真没啥好紧张的。
军衔就像是个“官”字,给你颁张证书,说明你在这儿有份儿!
监牢里当个老大,就是囚犯们结局的终点站。
张学良这小子心里门儿清!
他不是盯着刘乙光,他是在观察体制怎么给自己划上个结束符。

这俩家伙互看不顺眼整整二十多年的,但指着历史的鼻子告诉你,刘乙光也曾在关键时刻把张学良给捞了回来!
1937年夏天,张学良在雪窦山的别墅里被捅了一刀,刺客是个叫袁静枝的小姑娘,她背着把短刀,假装成亲友闯进了医院。
保镖反应慢了一点,张学良身边几乎没人拦着,刘乙光一下子冲了进来,没带任何武器就给对方挡住了,结果被划伤了左肩,鲜血狂喷,却紧紧抱住敌人不放。

这事儿后来张学良是个明白人,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他心里藏着一堆夸奖,但嘴巴就是不开,各种精彩都在心底翻滚,这一刀啊,真是刻骨铭心,忘不了!
1941年,贵州修文,张学良突然肚子疼得像被蚂蚁咬了一样,是阑尾出问题了!
山里没得医院,老天爷突然来场大暴雨。
刘乙冒着危险,派警卫下山叫来大夫,在破旧的小屋里搞定了手术。
光靠煤油灯照亮,疼痛就靠几口小酒消耗。
手术过后五天,张学良发烧像疯狂的火锅,怎么也不冷却。
刘乙整晚像只怼着不睡的猫,死活不肯动窝,也不想换个搭档。
这种时候,外面的人根本没法猜,张学良心里牢牢记着呢!
1962年,刘乙光被调到另一个地方,不再当张学良的助手,而是成了保密局的小顾问。
走之前来个小聚会,张学良还是老样子,坐那儿一动不动,脸上跟没擦油似的。
快到尾声时,他站起身来,嚷道:“这小子不光是我的死对头,还是我的大救星!”

现场安静得像是没人开口,连一声嗡嗡的附和都听不见,十秒钟就这么过去了。
那天晚上,张学良让手下送出一大笔现钞,说是送行的礼物,结果被蒋经国直接拒绝了。
刘乙光一溜烟儿就跑了,张学良被锁在新竹的山林里,转过身来连个影子都没瞧见,更别说听到啥脚步声。
1970年,刘乙光回到湖南参加永兴县的老乡聚会,走得是不声不响的。
有人问他当年帮张学良看家那么久的事,他就呵呵一笑,没说啥。
1982年,刘乙光走了,跟我们说拜拜了!
传到美利坚,张学良让人送花去悼念。
几年以后,有个记者过来问他对刘乙光怎么看,他嗖的一声就说:“他有他的主意,我心里更多的是想念。”

一句“想你”,把25年的恩怨都丢进了垃圾堆。
不是放过,是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
这不是谢你,而是认账!
他们折腾得青春都快没了,互相逼到极限,结果留下的全是挥之不去的回忆。
政界里没朋友,没敌人,全是命运上的对头!
#夏季图文激励计划第二期#
求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